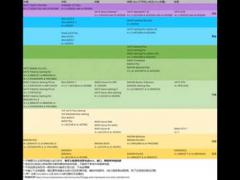上河图 (上河图描绘的是哪个城市)
上河图 (上河图描绘的是哪个城市)
走在路上的我被叫住了。
回头一看,是那个全身充斥着怨气的小组长。他拉着我的衬衫衣袖嚷嚷着:“K,你这个月是小组里KPI唯一一个不合格的,怎么回事?”
他所质问的对象有点心不在焉;这一向不善于对他超人似的地位阿谀奉承的组员此时显得有点过分呆滞,仿佛若有所思。的确,我当时才从洗手间出来,左手刷着公众号上的一篇未读完的文章,右手正试图往裤腿上蹭蹭擦干残余的水珠——谁叫公司所处的写字楼里的洗手间不配备烘干机;当然,我事实上也没想着要认真读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把它作为处理正事时期的消遣罢了,更何况此时我正在沿用着本科时期系统学到的科学探究方法试图回答一个严肃的问题:
“我是不是得痔疮了?”
是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连着四天我已经五次在通畅之后的善后处理之时擦到了血,而且这出血量似乎有着愈演愈烈的态势。作为没有医学背景的一个普通小职员,我也只能将最近的观测和百度上被众多广告所隐藏的些许得病者的症状进行尽量客观的比对,并试图在这些观察之中得到一个合理的结论;“业精于勤荒于嬉”,不得不承认,在荒废中度过的本科四年为我提供的理论知识仅仅能帮助我在当时以及格压线的姿态保过考试逃离补考,但一到真正运用的时候就慌了阵脚,露出应用水平不充沛的这一马脚来。
我叹了口气,想着自己或许真的要回去再翻开那本厚厚的基础导论教材了,而这单单是想想就勾起了大学时期头痛的回忆——不过,似乎是该理会一下那个小组长了;毕竟人家才借着族谱里发现的和老板是远房亲戚的东风上了位,还处在“新官上任三把火”的阶段,总得稍微尊重一下,以免他日后跑去和他那明面上亲戚实际上早已成亲爹的大人物参上一状。
“嗯好。”我嘟囔着。
“好啥好?绩效都不合格好个屁!我看你整天糊里糊涂,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他凑过头看看我的手机上的公众号文章,继续嚷道,“你看你还读什么《宋代艺术的文化背景》,一点点也不懂得脚踏实地。有这点时间去把你的问题弥补一下不行吗?”
这一骂让我彻底清醒了,我盯着他那条咄咄逼人的黄色带花的领带默默说道:“我马上去审核一下。”事实上我很清楚为什么这次没有过关:那和我交接的客户领了货后硬是坚持拖延几天、卡在财务审计后的第二天才愿意交付货款,而对待这种欠钱不还却当了大爷的人物,我这样的小业务员全然没有办法,更何况东奔西走的时候脑子里一直在处理那个重要的问题,以致于之前抱佛脚的努力之中藏有着一丝会令我被立即一脚踢开的破绽;可惜,正好这次被狐狸般狡猾的大爷发现了。
但我还是要这么回答,以免在走回到工位的那几十米的路上他一直在我耳边碎碎叨叨,像是那种孩提时在南方小城市里最讨厌的苍蝇。至于货款,这两天就应该来了,迟一天两天实际上也无所谓;反正这个月的绩效早就凉了——我是不打算再跑到大爷面前去碰一鼻子灰的,在公司里避上两天锋芒就是了。
我心里很清楚,他事实上也就出出风头显摆一下自己的小成就,而目前真要是动摇我这用时间堆叠出来的小职员的位置还是有点困难;看着他得意扬扬地离开着的背影,我也迈开步子往自己的位置上走去。不过这一插曲也阻断了我脑中核心问题的思考过程,我把手机锁上屏插到口袋里,试图去重拾丢掉的思路:今天在洗手间里的观察结果是什么样子的,而它能不能符合我前几日树立的假设?
说实在话,这是我好久都没有感受过的思维的乐趣。
回到位置上,邻座的A凑过头来问道:“被熊了?”
“对。”我闷闷回答道。
“习惯就好,小人得志是这样的。”
“嗯。”我用一个字终结了这一场背后的议论。之后的工作时光就在大家心照不宣的沉默中悄然溜走了。
(中间的第二部分)
和大多数乘坐地铁回家的人一样,挤在拥挤人潮之中的我喜欢挂着个耳机——且因为更多时候只是听个响,具体放什么曲目显得无关紧要:今天是古典,第二天可能就变成了嘶吼的金属乐。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更不谈隔绝开外界声音的是什么种类的音乐,我都只想在一天繁忙的工作后盯着地面发呆:
一双运动鞋、两双运动鞋、一双皮鞋(哦!其上是一双多么让人感到骄傲的有着良好做工的西装裤啊!)、一双板鞋、一双高跟鞋(都冬季了那双脚上为什么只有丝袜?)、还有我自己的那双灰黑色的鞋子。
总之,我会愿意把手头上处理着的核心问题拆分到每一天去慢慢品味,俗话说,“慢工出细活”嘛;当然这只是表面用来敷衍自己的托词,毕竟我早在孩提时代就明白不该去和身边的人讨论我正在思索的某些事情:一般的人是没有共情之心的,他们只觉得说出这个问题的我可笑到令人发指,但又碍于情面只能将那些谩骂藏匿在内心深处,再时不时窸窸窣窣地表露出来,像一只可笑的秋后蚂蚱。现如今,每当我看见别人因为类似的原因碰壁的时候往往会轻声笑一下,然后逼迫着自己将这种轻蔑压制掉;自然,与之相反的是,像我那新晋的小组长一样当着众人的面对我严厉指责的人也存在,而我也不奢望他们能在未来作出什么变化;我当然知道美好的理想主义有多么重要,不过年少时怀揣的那改变他人的雄图壮志早就随着时间慢慢碎裂消逝在空气中了。
其中一双运动鞋换成了很近地贴着的两双:男款和女款,而那双最令我感到兴趣的皮鞋已经踏着步子离去了;我透过耳机内对即将分崩离析的爱情的嘶吼,借着零星的杂音揣测着这双鞋大概会发出的声音:
(在人声鼎沸之中)啪嗒、啪嗒,(鹤立鸡群地)啪嗒、啪嗒,(走上电动扶梯了)啪嗒、——。
对啦!我还是得承认,所谓冠冕堂皇的拆分借口不过是为了掩饰潜在的对达成任务后必然出现的空虚的恐惧。
耳机里的爱情又一次消亡了,跟上来的是歌手对他颓唐人生的反思;板鞋也离开了、随后消失的是另一双运动鞋;我依然把头低垂着不让站着的人看到那双神采若有若无的眼睛——如果有人有机会看到的话会发现,它们亮了一下,代表着我在思考自己为什么会突然选择这个曲库,又因为得到了一个自我不愿意承认的否定性答案而暗淡下去了。
于是我决定去打个盹。
列车带着我继续那循规蹈矩的从公司所处的最人声鼎沸的三环向我所居住的六环的悠悠旅程。车厢内人的声音越来越弱,只剩下因机器在隧道中奋力用喧嚣摆脱自我的空洞的努力而导致的嘈杂的轰鸣。一般来说,其余的屈指可数的人把握住了空空荡荡带给他们的机会,尽力和周围的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便在沉浸在手机提供的欢愉之时不会感受到边上那位的挤压。当然也会有和我一样选择睡上一阵子的,他们精干的衣服无法遮拦自己精神在一天的压抑之后的颓唐。
我把耳机收了起来,听到那对鞋打情骂俏着下车的声音,在麻木之中暗暗艳羡着他们的幸福——上一次我当同类的人大概已经是五年前在大学校园内的时候了吧,那个时候虽然对着未来的天各一方有着些许的忧虑,但总是在无数个瞬时的愉悦之中忘却苦恼,甚至当时现在任职的这家公司给我提供的职位也冲淡了深夜时的辗转反思(那可不是一种留在北京的希望吗!)。不过她终归还是回到南方的家里去了,好像也屏蔽了我的朋友圈。
当我打算再度闭上眼的时候,直觉告诉我马上就到站了,而这时车厢内除了我就剩下那双高跟鞋了。于是我稍稍抬起头打量了一下:这是一朵只能在浓厚脂粉的辅助下开出小花朵的玫瑰,而我这么形容更多是因为她用冷漠竖起了笼罩在身子一边的刺;是的,这是一名多么骄傲的女人啊:她似乎全程都在刷着自己的手机,即便是有了再多的位置也不坐下来,好像车厢内的市井气和她的铿锵格格不入一样。
但我同情她:同样在晚高峰从市内往边缘地带走的我们大概有着相似的境遇,半小时后她说不定也会走进一个冰冷的狭小出租屋,盯着镜子看着脸上鲜艳的妆而任由泪水将它打散,再在夜里继续试图在素颜的脸上重又涂抹上娇嫩的粉色;对,我那个前女友当时就是害怕自己的美丽被这座城市蚕食干净才在毕业证书领到后就立马买好了回家的火车票。真的,那不过也只是旅途更长价格更贵的地铁,毕竟在我们当时屈指可数的恋爱末期那几天之中我亲身坐过类似的车到她的地方去,因此有着发言权。
下了车的我盯着她矗立在车厢里的身影时,感觉在看一块用粗暴线条雕刻的花岗岩雕塑,即便她透过脸上身上本来希望传递的是细微笔锋勾勒出的精细。
(依然处在中间的第三部分)
啊,北京又下雪了。
走在路上的我迎面对抗着北方泠冽的雪花的冲击。两旁的道路上是环卫工人已经从路上扫到一旁的小雪堆;在它们的白色之上,引人夺目的是黑色的污渍留下来的痕迹——也许来自路面也许来自肮脏的脚印——而它们交融的边缘的边缘地带的那种混杂的颜色像极了我这双鞋。
是的,我感觉我的双脚赤裸裸地踩在浑浊的雪上,即便它们已经裹上了厚厚的毛袜。
我突然禁不住越过了自己在地铁上设置的份额,问自己:“如果我真的得了痔疮,该怎么办?”想到的那一刹那我就后悔了,不仅是因为这一思考过程很可能是无用功(万一没得呢),更因为它所涉及的广度远远超越了我现在正在处理的问题:是的我说过,我实际运用知识的能力不强,故这个问题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思考。
我不愿意,真的。
但与之同时,我已经开始盘算自己捉襟见肘的银行卡余额能不能支撑手术、自己还有多少天的年假、要不要告诉父母、恢复期在家该怎么做饭,等等等等。
哦对还有,那个小组长会不会因此继续给我穿小鞋。
不得不承认,上班时的那一通训话对我还是有着一定的影响的,正因为这个,我决定摇摇头搁置这一切话题。于是在新调整的狂野的音乐的狂轰滥炸下,我成功再次放空了心态,在一片空白(嘿,还挺像正常的雪的颜色!)之中走出因寒冷而畏缩的步子。
直到手机弹出一条新闻说,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时隔十余年又要在故宫展览了。
我暗声骂了一句娘。
(这里是回忆!)
当年正好是一个孩子爱国之心爆棚的时候所以我求着父母带我坐着时间很长的火车从我家所在的南方城市到北京去玩真的当时的这座城市远远没有如今的奢华靓丽但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还是处处都像是金子建成的一样美而富裕人们的穿着打扮远远胜过当时灰扑扑的一家人而这一下子就把这一家的外地游客身份凸显了出来那个时候哪里有什么六环有的只是孩子对这城市一切的仰慕即便他当时还懵懂无知不知道这里能给它的居民带来更好的医疗环境教育资源甚至很多时候区区一个户口都能在未来成为当地人炫耀的资本但这个孩子能切身感到的是良好的物质资源以及那一顿让他永生难忘的肯德基天哪那份炸鸡虽然贵但真的好好吃现在吃的任何食物都比不上更别说当年家里母亲最常做的只能是蔬菜是的做一名北京人好像就是个难得的特权就算他同龄的孩子当时都因为这个词所指代的南方古猿的那层含义来嘲笑外地来的同学更何况他自己也曾经在那外地同学的眼中看见了自视清高和骄傲(哦我觉得现在说的这个同学像极了我那个小组长二者都是需要在别人身上寻找自我狂傲心态的满足而凭借的东西单薄又可笑)
作为经典的旅游目的地一家人在这所城市里必去的目的地就是北京故宫天呐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当时踏入这片森严的土地的时候便感受到的深切的逼仄感而这是再多的游客的人声鼎沸都无法消抹干净的无论是那设计那色彩还是布局都彰显着百年以来深入人心的特权在小民身上刻上的烙印我瞬间就想到了那个北京的同学并立刻感觉他身上有着一种将我们自动隔离开来的气息不得不说我当时便感觉先天给予我的出身就已然将我和百余年前的皇帝或是身边的自诩高贵的那些纨绔子弟分到不同的人生道路上都说当年革命革了皇帝老儿的命但我倒觉得皇帝老儿一直都存活在我们身边当然我也在想一点别的事情比如说皇帝他们当时住在这样的宫殿里会不会有一种束缚感即是一种就算他拥有全世界却也被世界关在这座富丽堂皇的监狱内的苦闷这么想想也许我那个同学也有类似的想法如果他不能来到我们这个比较贫穷的南方小城市的话身处在一群北京人之间的他根本没有任何竞争力甚至也会面临着更多比他地位更高的人施加的戏谑和嘲讽(真的更像那个组长了呢我已经开始构想他会见他新任亲爹时的那种卑躬屈膝了)
但一定要记住的是,这些思想不过是片面地存活在一个孩童的心里,而这拼图的完工是一阵子后的事情了——对于当时的他来说比这个更重要的第一是那顿肯德基,第二就是天安门广场上的升旗:对呀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央求父母要去北京的呀至于父母更不会去在乎这种虚无缥缈的想法毕竟生活的重担压垮了他们最后思索这些问题的空间对于这一代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塑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而看看好的东西也是重要的一环毕竟孩子也是身上的血肉总得给他们一点补偿平日内的缺席的时日的空间呀不过说到这里我也不得不开始反思毕竟我感觉我现在的浑浑噩噩远远无法到达父母对我的殷切期望可惜我也没有太大的悔意好吧回归正题我认为他们也是有着一些好奇心的总得看看这个封建时代的禁地不是吗看看那些对于北京的同僚来说触手可及的东西
那一天对父母来说真的是好日子除了能看到设计精巧的宫殿还正好撞上了《清明上河图》的展览在此之前我们对这个作品的感受就是它有着举足轻重的历史意义且绘画内容翔实丰满但在这之外对于谁是张择端这画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却没有任何感触我印象很深那天这幅画被束缚在长长的裱框里陈列在一间同样是长长的偏殿之内如织的游人脑袋之中我牵着父母的手试图冒着头凑近点仔细看看这幅画去在近处观察一下课堂上老师以神乎其神的名号所赞誉的艺术品当我几近能用鼻尖贴到那幅画上之时我终于看清了那些路面上桥面上缓缓行走的小人车马和别的陈列品是的不得不承认栩栩如生这个词不为过试想像这样仅用一点笔墨细微画上一笔便复活了一个有着活灵活现的动作的人物的能力除了像女娲这样的神灵还有谁能做得到呢(我真的不知道刚刚在说啥这不是明明还有作者张择端吗)这幅画是真的像宋代的城市呵方才用墨笔点出的人好像就能永生在这里坐着他们带有俗不可耐的气息却迸发出广袤生命力的市井活计它们冲破了四周的建筑或是那个裱框的阻扰破开了一切的迂腐和陈旧当然北京也有类似的生活不过在很长的设身处地体味这个城市的风情的时候我却常常能感受到它的地位造就的狂傲在居民身上塑造出的那种浮夸的气质这么说来我或许还更喜欢家乡的那个小城里的农贸市场可惜的是去年春节回家的时候或许是因为时间不对的缘故我在家乡里嗅到了从遥远的北京带来的那种让我恐惧的气质没错正是这种风气造就了地铁上那位可怜的姑娘或是我这样连有没有得痔疮都要斟酌半天的人物回到那幅画来说如果它描绘的不是市井生活而是宫廷之内的奢华我想我对它一定会嗤之以鼻吧
在它的鼓动下年少的我在离开那座小偏殿的时候对父亲说出了这一辈子以来我最后悔的一句话之一:
“爸,我以后想当个艺术家,把看到的一切都切实描绘下来。”
随之而来的便是暴风雨般的骤怒对于我父母这二位在工厂干了一辈子的实干家来说艺术家甚至是文科的学者研究的都是玄之又玄的东西在他们的心中和所追求的共产主义的达成是完全没有联系的即便他们自己也亲身在一旁看着这幅画不过我用心不在焉来描绘他们当时的状态绝对不为过这不过是一次走马观花目的是为了让这次旅行在日后成为更有意思的谈资见过张择端真迹的经历也绝对能吓倒身边的许多人对艺术他们只觉得是没有意义的亏钱东西且真正消耗了一个孩子的青春故他们一点点都不希望我和它有着任何瓜葛即便我前两天才参加了艺术比赛且获得了二等奖不过吧这个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参赛这一行为本身不过就是一种针对左邻右舍内的跟风行为的延伸并完全缘起于一名家长为了凸显孩子的与众不同时而提到的谈资对呀只有学习和刷题才是有意义的事情而当时的我已经能慢慢感受到未来一场场升学考试的压力即便我仍然对未来有着追求真的我通过那个比赛总会隐隐觉得自己有着投身艺术的天赋也因此浑身带着冲劲
这一追求现在看来多么可笑!
于是我收到了回复、斩钉截铁的那种:
“想这些有的没的干嘛?还不快点把成绩搞好?画个破画二等奖了不起了?”
从听到这句话开始到回到房间之后我从没说过一句话后来我真的就放弃了这个念想专门做父母欣赏的事情只可惜高考还是考不过省城的那一批人只能去一所不算特别突出的院校当然我的首选是这所学校必须地理位置在北京毕业了我也强制逼迫着自己要留在这个城市当然这一愿望在实现的同时也得到了身边困难的环境的反噬我逐渐发现自己开始举步维艰了是不是最后还得狼狈回到那个小城市呢我也不知道不过看似答案正在趋于肯定
的确是举步维艰在北京的雪中我开始慢慢感觉自己甚至已经要走不动路了我只能顶着风慢慢往前走完全忘记了去看身边的居民楼唉这就是我当年魂牵梦绕的地方吗想想我都暗自苦笑好吧我还有很多别的话想说但完完全全不知道该说什么事实上我都不愿意责怪我的父母他们也什么都不懂完全不能理解什么是梦想我也只得靠自己努力只可惜我努力了这么久也没做出什么价值来真的是令人发笑:
唉!!!
(结尾的第四部分)
当我小声呓语着爬到公寓楼门口的时候收到了母亲的短信,上书:“《清明上河图》展又开了,你可闲暇时去看看!记得你小时候很喜欢!”我苦笑一声,愈发觉得自己无法真正去责怪二老——他们实质上还是称职的父母亲,也正是如此才试图避免我走上他们所认为的歧途。我想了想要不要把目前正在思考的问题分享给她,不过在快要点发送的时候把编辑好的文字删除了:报喜不报忧似乎已经成了我在北京的这段时间学会的最有用的人际相处技能。
于是我回复:“好!我也看到了。”末了又配上一个好似在奚落对方的“微笑”的表情。
哈!七点后的时间都是我的!小时候常常希望能有独属于自己的一到两个小时去思考一些有的没的的内容,可如今面对下班后的那些空余时间的我常常感受到一阵空虚。按惯例,我将羽绒服脱掉,信手扔到房间里那张小小的床上;很快跟着扑倒在床上的就是我的躯体——“咣当”。在这大约能算作完全自由的空间和时间里我完全不需要去思考任何棘手的问题:只要先点一份外卖(牛肉汤吧!正好还有一张减八元的满减券),之后就可以一直玩手机去真正放空我的心态;或许等到晚上有时间了,可以稍微回味一下尘封了许久的本科教材,但前提是要先刷完今天推送的所有视频。
我半躺在床上,一只手刷着工作时网站上上传的视频,另一只手无目的地抓着自己的头发,把早上打理好的这一团毛重又变得和鸡窝一样。哦对了,我最近特别喜欢花两倍速看某些视频,因为这样能感受到那种压缩后在一半短的时间里汲取一样多内容的快感,虽然以很快的时间刷完之后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无所事事所带来的空虚。我常常告诫自己要在这段时间内去读一两本书,但手却无数次刷新着屏幕上的视频推荐列表,以期找到一个对自己路子的视频来再消磨掉一点时间。
也不知具体过了多久,外卖终于到了。我推开门,那穿着制服的小哥把袋子里的温热的汤送给我;当然,他时不时在用余光关注着我头顶的那团鸡窝。
“是*先生的外卖吗?天气冷,汤可能会变凉,请见谅。”
“是我,谢谢你。”我手里还捧着手机,尽可能试图盯着屏幕里的游戏世界望,因此并不想在乎他究竟说了什么,或是那双眼睛里透露出了多少对我如今不修边幅的好奇感(难道我的头发真的就那么乱吗,我是不相信的)。拿右手接过外卖的时候我碰到了他拎着塑料袋的红红的手,不禁抖了一激灵,突然意识到外面的世界有多么寒冷,而我或许是因为才从寒风中走回来的缘故,内心的火苗好似正在逐渐熄灭,纵容自己的外表也慢慢凝结出寒冷的冰晶。
我后怕地关上门。
不过当室内的暖气重又充盈着全身的时候,游戏的世界重又捕获了我的注意力:对呀,我并没有时间去思考这些目前看来无意义的问题嘛!我架起手机,掀开盖子,任凭汤碗上的热气在解除对它们束缚后尽情地升腾起来。冬季温暖的汤下肚之时,被这些热气糊住眼睛的我好似重又捕获到了一缕温暖的人情味。
其余的气体(当然我想起来,物理书上说这应该是小水珠)依旧向着天花板由快而慢地逸开,似乎像是摆脱了初步逃离的那种狂喜,开始悠悠地审视这个世界。盯着手机的我没有看到的是,它们重又急切地聚拢在一起,簇拥着一个从无到有的若即若离的巨型身躯。与之相反的,在冬季暖烘烘的房间的烘烤、手机内游戏解说愈发明晰的催眠作用、以及白茫茫的气体营造出的混沌感的一并作用下,我的意识渐渐开始迷离,机械地盯着屏幕嘬着碗里的鲜汤(也许其中加了不少味精)。
直到冥冥之中好似有个力引领着我抬起慢慢昏沉的头,去竭力辨别着那云雾缭绕着的身躯:那是一条龙,货真价实,只不过祂的身躯不是许多人所想象的绿(针对这一点我觉得,当今的社会对蛇绿身子的普遍认知已然被依葫芦画瓢着嫁接到龙这种难以被语言描述的神兽之上了),而是那种淡淡的符合着我房间里氛围的白。
祂的眼睛盯着我游离的双眼——我在努力辨别这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祂的面部表情模糊不清宛如一场奇幻的梦里的人物,但那双眼睛内的神采却无比真实又咄咄逼人。是的,牛肉汤碗还是温热的,手机也仍在播放一样的视频,可它们都变得虚幻了起来。在祂(好像)没有张口的情况下,我内心里涌现出一阵低沉的声音:「日安」。
我发现我好像也不再用张开口就能传达自己的意思了:“日……安。你……哦不,您为什么出现在这里。”
「你倒是没质疑我的真实性哈。」
“是吧……也没有……至少我不该问这个。”我感觉身边的一切似乎都在变得虚幻,而狭小的空间里仅剩下“我们二人”,而大脑好像是在空空荡荡没有一本书的图书馆里寻觅紧要学术资料的学生,跑遍了所有角落也找不到任何能印证这些事情的线索。
「有趣。」祂顿了一下,「不是一般人见到我后的风格。」
「当然我知道你在想这个问题,不过是没有放到口舌上罢了。」
“啊……”
「哦,现在真的没有什么想法了。」
「打算去看《清明上河图》展吗?第二次?」
“你来做什么?”我的思想里传达着急切和困惑。
「不要着急。你可知,龙也是会无聊的,那总得做点什么打发寂寞不是。」
“啊刚刚不该说你的……您为什么会知道清明上河图的事?为什么不偏不倚问到这个?”我的“嗓音”更加急切了。当然,此时整个房间里除了解说游戏的主播的声音外一片静默;我也沉浸在对话中忽视了它的声音和画面里激烈的搏杀。
「称谓无妨,我也不是没见过向我三跪九叩的人。至于那画,你不觉得它画得格外出彩吗?」
“的确精彩,”与之同时我在又一次回忆着那些和那幅画和我息息相关的元素:“童年……北京……东京汴梁……小市民们的群像……画画……该停止啦!可是我却抑制不住自己怎么办……地位……毁灭和失望……”天呐,这就是确确实实的梦呓。
龙打断了这时刻能走到无穷无尽的思绪:「我似乎不该提到这件事的,不过既然已经出口,让我稍微提一嘴吧:约一千年前我曾经到当年的东京(是这个城市吧)去观摩过一回,现如今那个时代早就不见了,我也只能靠看那画来缓解现在看不见这一幕的惆怅。你知道,回忆过往千年的那些骤变是一件很让我唏嘘哀叹的事。」
「此外,在故宫,我还能看看你们是怎么在建筑上刻画我的。这可是不错的笑料。」
“你觉得那是幅好画?”
「当然。我喜欢的东西不多。」
「希望你再去看一眼那幅画吧,那可真是个有着艺术气息的好作品。作为这一要求的报偿,我可以允诺你的一个愿望。」
能许一个可以被满足的愿望当然是好的;我想都没想就满口应承下来。
「说吧。」
我感觉我把一天的精力都积攒在这个时刻了,迸发出来的是:“那请您帮我看看我究竟有没有得痔疮吧我在洗手间处理完后都发现屁股流了好多血自己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真的我已经想这个问题好多天了总得要有个答案吧如果有的话顺带帮我治愈好不好希望这一切能算作一个愿望?”
一下子说完这一串连珠炮后的我已然失去了神采,身子摊在桌子上。
「果然是这个吗。」龙默默评论着,话中带着一抹被巧妙隐藏了的哑然失笑的意味,「好吧。」祂的身影慢慢减小,直到消失。
房间里只剩下了一些余留的白汽,它们很快就消散开去了;随着视频里最后一句结束语被说完,手机也识相地消匿了自己的声响。
——仅剩下我一个人在方才逼仄感的余威下大喘气。

放一张此时比较契合主旨而非内容的图吧, cr. H. Xu
以上就是(上河图 (上河图描绘的是哪个城市))全部内容,收藏起来下次访问不迷路!